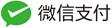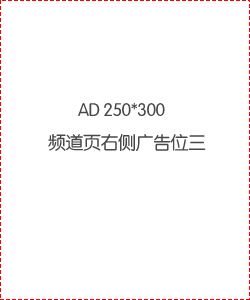一代奇人——东方朔
东方朔(前154~前93),复姓东方,名朔,字曼倩,平原厌次(今山东陵县)人。博学多识,滑稽善辩,诙谐足智,机敏过人。但言谈放荡,行为不检,近似癫狂。事汉武帝为郎,以滑稽善辩得宠,官至太中大夫、给事中。但终身不得大用。晚年有所转变,颇有善言直谏,但仍诙谐不改。其事迹史书多有记载,但评价不一。刘向视其为神仙家,收入《列仙传》;司马迁视其为滑稽家,与淳于髡、郭舍人等并写入《史记•滑稽列传》;《汉书》单独为之立传。有赞曰:“其滑稽之雄乎”!(《汉书•东方朔传》,下引此书不再加注)评说贬多褒少。而《汉书•艺文志》著录东方朔文二十篇于杂家类。今人将东方朔列入文学家。如何评说,难定一格。
滑稽诙谐 喜剧人生
《汉书•东方朔传》载东方朔到长安上书自言身世云:
臣朔少失父母,长养兄嫂。年十三学书,三冬文史足用。十五学击剑。十六学《诗》、《书》,诵二十二万言。十九学孙、吴兵法,战阵之具,钲鼓之教,亦诵二十二万言。……又常服子路之言。年二十二,长九尺三寸。目若悬珠,齿若编贝。猛若孟贲,捷若庆忌,廉若鲍叔,信若尾生。若此,可以为天子大臣矣。
此言东方朔二十二岁到长安上书。而《列仙传》说他曾“久在吴中,为师数十年”,显然不足信,传闻而已。《史记•滑稽列传》云:“武帝时,齐人东方生,名朔,以好古传书,爱经术,多所博观外家之语。朔初入长安,至公车上书,凡用三千奏牍。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”,仅能举动。汉武帝读两个月才算读完。
上书说了什么,除《汉书•本传》录其自言身世一段外,各书均不见有录。但从自言身世一段可以看出,其中不乏自我吹嘘。故班固说他“言辞不逊,高自称誉。”因此汉武帝看了,虽奇“伟之”,但未立即诏用,只使其“待诏公车”。“公车”,汉设机构,属卫尉。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徼宫,天下到京上书言事以及征召到朝廷的人士,都到公车。
东方朔待诏公车,久不见诏见和录用,俸禄又薄,急了。于是想法引起皇帝重视,从而召见他,以便进身。有一天他编造谎言,吓唬在宫中养马(或御马)的矮子———侏儒说:“皇上以为你们身单力薄,种田不及常人,当官当不了,当兵拿不动兵器,于国无用,白费国家衣食,要尽杀你们。”侏儒们吓得哭了。东方朔又教其主意说:“过一会儿皇上从这里经过,你们可以向皇上叩头请罪。”不一会儿汉武帝果然从这里经过,侏儒忙向前号泣叩头。汉武帝不知为何,便问:“这是为什么?”侏儒们哭着说:“东方朔说皇上要杀掉我们。”为了弄清原因,便召东方朔问道:“你为什么要吓唬侏儒?”东方朔说:“我活着要说,死了也要说,侏儒身长三尺余,拿一囊粟,钱二百四十。我身长九尺余,也是一囊粟,钱二百四十。侏儒要撑死,我东方朔要饿死。如果侏儒可用,最好改变待遇。如不可用,干脆赶他们走,不要白费长安的粮米。”一席话把汉武帝说笑了。原来如此。汉武帝明白了东方朔的用意,于是“使待诏金马门,稍得亲近。”
金马门者,宦者署门也。门旁有铜马,故曰“金马门”。汉代制度,凡征召来的士人,都待诏公车。只有学识优异才能出众者,才得待诏金马门。金马门比公车进了一步,设在宫中,能常见皇帝,故曰“稍得亲近”。
东方朔用这种恶作剧的方式作为晋身之阶,实在有些损德,但他取得了成功:待诏金马门,得入宫中,有较多机会接近皇帝。东方朔并不因此满足,而是得寸进尺,千方百计寻机炫耀自己,以期进一步接近皇帝。
有一天,汉武帝召集诸多术数家“射覆”(即将某物置于反扣的器皿之下,令人猜测),放置一守宫(壁虎)于覆盂下,令术数家们猜测。众术数家皆射不中。东方朔向前请求汉武帝说:“臣曾学习过《易》,请让我来猜。”于是他“别蓍(分开卜卦用的蓍草或蓍龟)布卦”,算了一算说:“臣以为像龙但无角,似蛇而又有足,爬起来跂跂脉脉,善于攀缘墙壁,不是守宫就是蜥蜴。”射中了,汉武帝称善,赐帛十匹。复使猜射他物,连连射中,皇帝也连连赐帛。
时有幸倡郭舍人,滑稽不穷,得武帝宠幸,常侍左右,在旁看得眼红,就说:东方朔发狂,侥幸射中罢了,并不是他的术数极精。我愿意令东方朔再射一物。他射中了,打我百棍;不能射中,赐给我帛。于是暗置一树上“寄生”于盂下,令东方朔猜射。东方朔说:“是窭薮也。”舍人认为东方朔猜错了,忙说:“果知朔不能中也。”东方朔辩说:“生肉为脍,干弱为脯;著树为寄生,盆下为窭薮。”不知东方朔是杜撰,还是真有此典故。舍人不知,汉武帝认可。于是“令倡监榜(棒打)舍人”。舍人不胜痛苦,大声呼叫。东方朔在旁幸灾乐祸,火上浇油,笑说:“咄!口无毛,声嗷嗷,尻(屁股)益高。”舍人愤怒地说:“朔擅抵欺天子从官,当弃市。”于是汉武帝问东方朔:“为何诋毁舍人?”朔答曰:“臣哪敢诋毁他,是与他说隐语罢了。”武帝问:“隐语怎么说?”朔说:“夫口无毛者,狗窦(腚)也;声嗷嗷者,鸟哺瞤(雏鸟)也;尻益高者,鹤俯啄也。”又把舍人骂了一顿。舍人不服,并企图寻机报复,便说:“臣愿复问朔隐语,不知,亦当榜。”即妄为谐语曰:“令壶龃,老柏涂,伊优亚,狋吽牙。何谓也?”朔曰:“令者,命也。壶者,所以盛也。龃者,齿不正也。老者,人所敬也。柏者,鬼之廷也。涂者,渐洳径也。伊优亚者,辞未定也。狋吽牙者,两犬争也。”舍人所问,朔应声辄对,变诈锋出,莫能穷者,左右大惊。上以朔为常侍郎,遂得爱幸。
东方朔依其广博的知识,精到的术数,机敏的辩才和滑稽诙谐的隐语,又一次用恶作剧的方式炫耀了自己,戏侮了他人,而取得了汉武帝的欣赏和爱幸。因此,“上(汉武帝)以朔为常侍郎,遂得爱幸”。
东方朔得宠之后,更加有恃无恐。不仅言谈放荡,玩世不恭,而且举止无礼,近似癫狂。
有一次,三伏天,“诏赐从官肉”。天晚了,负责分肉的大官丞还没有来。东方朔等不及,便擅自一个人拔剑割肉而去,并对从官们说:“伏日当早归,请受赐。”大官丞以为无礼,告到皇帝那里。第二天汉武帝问东方朔:“昨日赐肉,为什么不待诏令就独自拔剑割肉而去?”东方朔忙免冠谢罪。武帝说:“先生起自责也。”叫他自我检讨。东方朔再拜曰:“朔来!朔来!受赐不待诏,何无礼也!拔剑割肉,一何壮也!割之不多,又何廉也!归遗细君(老婆),又何仁也!”汉武帝笑了,说:“叫你自责,你反自誉。”复赐酒一石,肉百斤,令归遗细君。
东方朔的滑稽诙谐,以及汉武帝对东方朔的宠幸由此可见一斑。
说到“归遗细君”,有必要交代一下。即东方朔好女色,出手大方。皇上所赐钱财,大多用在了女人身上。《史记•滑稽列传》说东方朔“徒用所赐钱帛,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。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,更取妇。所赐钱财尽索之于女子。人主(皇帝)左右诸郎半呼之‘狂人’”。
东方朔行为不检,近似玩弄女性。这种污德“狂人”,汉武帝不仅不责怪,反而赞许,对称东方朔为“狂人”的诸郎说:“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,若等(你们)安能及之哉!”
正因有皇帝的赞许,东方朔便有更狂的表现。《史记•滑稽列传》载:有一次东方朔走在殿中(去坐席),有个郎对他说:“人皆以先生为狂。”东方朔不以为耻,更不以为忧,反而说出更狂的话。朔曰:“如朔等,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。古之人,乃避世于深山中。”等坐席中,饮酒至酣,又据地而歌曰:“陆沉于俗,避世金马门。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,何必深山之中,蒿庐之下。”意思是说隐于朝廷,既可避世全身,又有高官厚禄,身伴天子,言谈可任意挥洒,丰厚的俸禄可以纵情享受,何必像古人那样避世于深山,蜗居于草庐之下,去受苦呢?
这种言论,按汉律死罪有二:一是欺君。在朝当官,就要事君竭力,尽忠效命。否则官居要位,窃取厚禄,只为个人享受和“全身”,就是“欺君”。二是有辱当朝。如若要问:“你避的什么世,全的什么身?”岂不得出答案是当世为“乱世”,人命“自难保”吗?这样有辱当朝,岂不也是死罪?再说,贤士归隐,不为当世所用,也可定为死罪。西周初年,姜太公就封至齐,听说有贤士(华士、狂矞)兄弟二人,隐于东海,声言:不臣天子,不友诸侯,耕作而食,拙井而饮,无求于人,无上之名,无君之禄,不事仕而事力。太公闻知,以为“世之贤士不为君用,非明主之所臣”,干脆把二人杀掉了。(事见《韩非子•外储说右二》)
这些掌故和律条,东方朔不能不知,而敢公开声言是隐于朝廷,“避世全身”,这不是狂到家了吗!
东方朔还“任其子为郎,又为侍谒者,常持节出使。”并教其子学他,也“避世全身”于朝廷间。
当然,东方朔可能心中有数:一是他以滑稽诙谐得宠,连恶作剧也屡试不爽,更何况“常在侧侍中,数召至前谈语,人主未赏不说(悦)也”(《史记•滑稽列传》)。二是东方朔确实有广博的知识,又有机智善辩的才能,总能说转皇帝,变不利为有利。是之谓“艺高人胆大”吧。其知识渊博,以下两事可见一斑。
《史记•滑稽列传》载:有一次,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东方朔辩论,博士们一齐向他发难说:“苏秦、张仪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以干万乘之主,都做到了卿相的大官,使后世受惠,你读了那么多书,博闻辩智,竭力尽忠于汉武帝这样的圣明之君,积数十年,才做到了一个小小的侍郎,这是什么缘故呢?”东方朔以时势不同作答,纵论战国时代和当世形势之不同。战国时期,天下分裂,列国竞雄,“得士者强,失士者亡,故说听行通。……今非然也。圣帝在上,德流天下。诸侯宾服,威振四夷,连四海之外以为席,安于覆盂,天下平均,合为一家,动发举事,犹如运之掌中。贤与不肖,何以异哉?……使张仪、苏秦与仆(我,东方朔)并生于今之世,曾不能得掌故,安敢望常侍侍郎乎!”又引传曰:“天下无害灾,虽百圣人,无所施其才;上下和同,虽有贤者,无所立功。”这是所谓“时异则事异”,“你们有什么可怀疑我的呢!”“于是诸先生默然无以应”。
又:建章宫后阁重栎中出来一物,其状似麋。听说后,汉武帝去看了,问左右群臣习事通经术者,无人知晓。诏东方朔去看。东方朔说:“我知道,希望赐给美酒粱饭让我大吃大喝一顿,我就说。”诏曰:“可。”但东方朔过了一会儿又说:“某处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,陛下若赐予我,我就说。”诏曰:“可。”于是东方朔这才说:“所谓驺牙者也。远方当有来归顺的,而驺才预先出现。”过后一年左右,匈奴混邪王果然率众十万来降归汉,证实了东方朔的预言。因此,汉武帝“复赐东方生钱财甚多”。
东方朔自视甚高,满朝文武,“自公卿在位,朔皆敖弄,无所为屈。”汉武帝曾问朔:“方今公孙丞相(弘)、儿大夫(宽)、董仲舒、夏侯始昌、司马相如、吾丘寿王、主父偃、朱买臣、严助、汲黯、胶仓、终军、严安、徐乐、司马迁之伦,皆辩知宏达,溢于文辞,先生自视何如比哉?”东方朔戏弄地说:“臣观其砊齿牙,树颊胲,吐唇吻,擢项颐,结股脚,连睢尻,遗蛇其迹,行步睠旅,臣朔虽不肖,尚兼此数子者。”
汉武帝以知识才能提问,东方朔却以形态体貌的某些缺点戏弄大臣,还大言不惭地说,能兼此数子。其狂妄、放荡,进对言辞,“皆此类也”。
直谏诚嘉 曲意可悲
东方朔天性诙谐,虽难自改,但是也有忠直的一面。班固说他:“然时观察颜色,直言切谏,上常用之。”如建元三年(前138),汉武帝始微服出行。与左右能骑射者约于诸殿门,常常夜出,自称平阳侯。猎于南山下,驰射鹿、豕、狐、兔,手格熊罴,践踏农田禾稼。百姓号呼谩骂,地方官(雩、杜令)欲抓捕之。驰猎所到之处,私置更衣之所十几处。又决定圈占阿城以南,周至以东,宜春以西地,扩建上林苑。当时东方朔在旁,上前进谏,陈《泰阶六符》之奏,劝之以应天顺人:“臣闻谦逊静悫(谨慎),天表之应,应之以福;骄溢靡丽,天表之应,应之以异。”又说:“夫南山,天下之(险)阻也。……厥壤肥饶”,物产丰富,万民所仰足,今扩建为苑,上乏国家之用,下夺农桑之业,又坏人冢墓,发人室庐,令幼弱怀土而思,耆老泣涕而悲,“故务苑囿之大,不恤农时,非所以强国富人也。”接着又以“殷纣作九市之宫”、“秦兴阿房之殿”,招致灭亡的教训为鉴,劝武帝深省。
汉武帝虽未采纳东方朔的意见,“遂起上林苑”,但却因《泰阶》之奏,乃拜朔为太中大夫、给事中,赐黄金百斤。
东方朔的谏言也有被采纳的,如奉觞上寿,劝武帝止哀:隆虑公主之子、汉武帝的外甥兼女婿昭平君,恃势骄横,醉杀主傅,狱系内宫。廷尉论罪,武帝许之。但又哀痛不已,说:“吾妹老有这么一子,死时托付给我”。但法不容情。于是垂涕叹息,哀不能自止。正在这时,朔前上寿,曰:“臣闻圣王为政,赏不避仇雠,诛不择骨肉。《书》曰:‘不偏不党,王道荡荡。’此二者,五帝所重,三王所难也,陛下行之,是以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,天下幸甚!臣朔奉觞,昧死再拜上万岁寿。”武帝这才起来,进入省中。但到了晚上又召东方朔责问说:“传曰:‘时然后言,人不厌其言’,今先生上寿,时乎?”责东方朔上寿不是时候。东方朔忙免冠顿首,谢罪说:“我听说乐太甚则阳溢,哀太甚则阴损。阴阳变则心气动,心气动则精神散,精神散而邪气及。销忧者莫若酒。臣朔所以上寿者,明陛下正而不阿,因此止哀也。”由此不仅化解了武帝的不满,并且得到了赏赐和复用———“复为中郎①,赐帛百匹”。
东方朔的直言切谏又一次被采纳,那就是敢逆“龙鳞”,阻止武帝的宠幸之人“董君”入宣室赴宴。
“董君”何许人也?汉武帝姑母馆陶公主号“窦太主”的近幸(情人),且得武帝之宠,称其为“主人翁”的董偃。窦太主尚堂邑侯陈午。午死,窦太主寡居。年五十余,守寡不住。而养在其第中的董偃,少年“姣好”。至十八而冠,即得近幸。“出则执辔,入则侍内”。“以主故,诸公接之,名称城中,号曰‘董君’。”因劝公主献长门园,而使汉武大悦。又假称公主有病,骗得汉武帝临视。董偃得机侍宴,武帝大为欢乐。于是“董君贵宠,天下莫不闻。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凑董氏”。董氏也常从皇帝游戏宫中,猎逐园林,观看斗鸡蹴鞠之会,角逐狗马之足,使“上大欢乐之”。
有一天,汉武帝为窦太主置酒设宴宣室,使谒者引董偃入内。时东方朔当值,持戟立于阶侧,上前阻止,曰:“董偃有斩罪三,安得入乎?”皇上问:“这怎么说?”东方朔大声说:“偃以人臣私侍公主,其罪一也。败男女之化,而乱婚姻之礼,伤王制,其罪二也。陛下富于春秋,方积思于《六经》,留神于王事……偃不遵经劝学,反以靡丽为右,奢侈为务,尽狗马之乐,极耳目之欲,行邪枉之道,径淫辟之路,是乃国家之大贼,人主之大蜮,偃为淫首,其罪三也。”武帝默然不应,良久曰:“吾业已设饮,后而自改。”东方朔说:“不可。夫宣室者,先帝之正处也,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……”汉武帝说:“善。”于是诏止,“更置酒北宫”,“赐朔黄金三十斤”。
东方朔又一次善言正谏,是武帝问治国化民之道,东方朔对以孝文之治。《汉书》本传载:
时天下侈靡趋末,百姓多离农亩。上从容问朔:“吾欲化民,岂有道乎?”朔对曰:“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康上古之事,经历数千载,尚难言也,臣不敢陈。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,当世耆老皆闻见之。(文帝)贵为天子,富有四海,身衣弋绨(黑色厚缯),足履革舄(硬生皮鞋),以韦(不加饰的韦)带剑,莞蒲为席,兵木无刃(不治利兵),衣(乱絮)无文(纹饰),集上书囊以为殿帷,以道德为丽(美),仁义为准。于是天下望风成俗,昭然化之。今陛下以城中为小,图起建章,左凤阙,右神明,号称千门万户;木土衣绮绣。狗马被(披)缋(五彩毛织物);宫人簪玳瑁,垂珠玑;设戏车,教驰逐,饰文采,聚珍怪;撞万石之钟,击雷霆之鼓,作俳优,舞郑女。上为淫侈如此,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,事之难者也。陛下诚能用臣朔之计,推甲乙之帐燔之于通衢,却走马示不复用,则尧舜之隆宜可与比治矣。《易》曰:‘正其本,万事理,失之毫厘,差以千里。’愿陛下留意察之。”
这篇谏言刚直不阿,正义凛然,敢拿汉武帝之奢侈与孝文帝之节俭对比,直言当今天子之失,是要有胆量、有卓识、有正义在胸的,弄不好会招致杀身之祸。但因言皆有据,道理明正,汉武帝虽不改其奢,但也没有怪罪。
东方朔的直言切谏,还有两事。
其一,劝止武帝浮海求蓬莱。《资治通鉴•汉纪•孝武皇帝》载:元年(前110),汉武帝封泰山后,听信方士之言,以为蓬莱诸神可得,欣然东至海上,欲自浮海求之蓬莱,群臣谏不能止。东方朔谏曰:“夫仙者,得之自然。……若其有道,不忧不得;若其无道,虽至蓬莱见仙人,亦无益也。臣愿陛下第还宫静处以待之,仙人将自至。”汉武帝这才罢了。
其二,《史记•滑稽列传》云:
至老,朔且死时,谏曰:“《诗》云:‘营营青蝇,止于蕃。恺悌君子,无信谗言。谗言罔极,交乱四国。’愿陛下远巧佞,退谗言。”帝曰:“今顾东方朔,多善言。”怪之。居无何,朔果病死。传曰:“鸟之将死,其鸣也哀;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。”是之谓也。
这段文字没有前因后果。东方朔为什么有此谏言?《资治通鉴•汉纪•孝武皇帝》有段记述:太子造反,兵败逃亡。武帝怒甚,欲必发兵诛之。群臣忧惧,不知所出。壶关三老茂上书谏说以骨肉之情:“太子造反,是因奸诈之臣用上命迫蹴太子,太子以救难自免罢了,并无邪心”。于是引《诗》曰:“营营青蝇,止于蕃。恺悌君子,无信谗言。谗言罔极,交乱四国。”书奏,武帝感悟,然尚未说赦免太子。
但这段话记于征和元年(前91),壶关三老茂名下。时朔已于两年前病故,引《诗》一样,是两回事,引用相同,还是同一件事,记事有误?不敢断定。东方朔的“直言切谏”,所见大体如此。
晚年转变 终吐真言
东方朔自视极高,欺诋下人,傲弄大臣,有点目空一切,除了皇帝,似乎谁也不放在眼里。自言诵《诗》、《书》二十二万言,兵法二十二万言,又学战阵、钲鼓之教,二十二岁身长九尺余,堂堂仪表,勇若孟贲,捷若庆忌,廉若鲍叔,信若尾生,文武全才。“若此,可以为天子大臣矣。”“为天子大臣”这是东方朔的初衷宏愿。在他自己想来,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,事与愿违。尽管他费尽了心机,表现自己,但就是不见重用,只是“常为郎,与枚皋、郭舍人俱在左右,诙啁而已”。对此,东方朔当然不会甘心。
怎么办?改变方式。直的不行,来曲的。首先,曲意奉承,吹捧皇帝。有一次汉武帝问他:“先生视朕何如主也?”东方朔说:“唐虞之隆,成康之际,未足以喻当世。臣伏观陛下功德,陈五帝之上,在三王之右。非若此而已,诚得天下贤士,公卿在位,咸得其人矣”。于是把当朝大臣比做周、邵二公、孔子、太公、毕高公、皋陶、后稷、伊尹、伯夷、管仲、百里奚、子产等,把武帝说得大笑。显然汉武帝听出了其中的奥妙:东方朔在说违心的话,曲意奉承而已,与前“自公卿在位,朔皆傲弄”,完全相反;与前之“直言切谏”批评武帝之失和陈“化民之道”,也大相径庭,故汉武帝大笑,以滑稽诙谐之言视而置之。这一手又失灵了。
汉武帝雄才大略,内兴制度,外事四夷,国家多事,用人之际,广揽英俊。“程其器能,用之如不及。”自公孙弘至司马迁,满朝文武,皆得其位。而东方朔则常与幸倡俳优为伍,实在令其难忍。没有办法,只好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,因自讼独不得大官,欲求试用。“其言专用商鞅、韩非之语,辞数万言,终不见用”。朔因著论,设客难已,用位卑以自慰谕。又作《非有先生论》,借非有先生之口,以谏吴王为名,既发牢骚,又抒政见;既大讲仁义大道之理,又借机讥评当世。由此看来,东方朔晚年压抑过于深重,实在“直”不起来了。直到临死,再无顾忌时,才再敢一吐真言,谏曰:“愿陛下远巧佞,退谗言”。一语道出久积胸中的块垒,使汉武感到奇怪,说:“今顾东方朔多善言?”
东方朔的著述颇多,但流传下来的不多。《汉书•艺文志》著录二十篇,见诸《本传》者,有:《答客难》、《非有先生论》、《封泰山》、《责和氏璧》、《皇太子生谋》、《屏风》、《殿上柏柱》、《平乐观赋猎》、《从公孙弘借车》及八言、七言(诗)上下等。前二篇,班固称其最佳,故录有全文,其余仅具目录。班固认为:“凡刘向录朔书具是矣,世所传他事,皆非也。”注引师古曰:“谓如《东方朔别传》及俗用五行时日之书皆非事实也。”班固此说自相矛盾。他在《汉书•艺文志》著录朔书二十篇于杂家类,这里怎么又说朔书就是这十篇呢?再说,就其《传》中所见,上书三千奏牍,上《泰阶》之奏和“陈农战强国之计”数万言,难道不是东方朔的著作吗?除此之外,《隋书•经籍志》著录东方朔《十洲记》和《神异经》于史部地理类。《神异经》有争议,或谓后人所作,而《十洲记》今已大体肯定是东方朔撰。
东方朔的思想,由于他“言不纯师,行不纯德”,班固说他“诙达多端,不名一行,应谐似优(俳优—演员),不穷似智,正谏似直,秽德似隐”,很难说他是什么家。但其思想的基本倾向,还是可以从其“正谏”之辞和著作中看出的。其《泰阶》之奏、“宣室之谏”(阻董偃入宣室)表现他重礼重义,尚俭禁奢。重本抑末,基本观点倾向儒家。这与其《签客难》和《非有先生论》所表现的思想基本一致。东方之论,以此二篇最为完整,最为班固称道,说:“朔之文辞,此二篇最善”。的确此二篇表达思想最完备而真实,基本体现的是儒家思想。
其一,讲修身、行仁义。如其《签客难》,虽是为自己不得大官自解自慰,说时异事异,生不逢时,无所用武,但又说:“虽然,安可以不务修身哉!”“苟能修身,何患不荣!(姜)太公体行仁义,七十有二设用于文武。”并引《诗》云:“礼义之不愆。何恤人之言?”强调修身,体行仁义。
其二,主张褒有德,禄贤能;退谗言,远巧佞。这是在东方朔言论当中屡见的。他常以历史上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为例,以桀、纣与汤、文对比,说明信谗言、用巧佞的危害,而用贤能、褒有德的益处:桀、纣“放戮圣贤,亲近谗夫”,“遂往不戒,身没被戮,宗庙崩弛,国家为虚”。而商汤、周文王,得伊尹、姜太公辅弼,“本仁祖义,褒有德,禄贤能。诛恶乱,总远方,一统类,美风俗,此帝王所由昌也。上不变天性,下不夺人伦,则天地和洽,远方怀之,故号圣王”。因此说,帝王应当“举大德,赦小过,无求备于一人”。这些理论也是儒家的东西。
当然,东方朔所学驳杂,不拘一说,有许多自相抵牾之处。他既“非夷齐而是柳下惠”,认为伯夷、叔齐兄弟二人,耻食周粟,隐遁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,而至饿死,实不可取,戒其子不要学他。要学老子,避害于朝廷间,“以隐玩世”,故曰“首阳为拙,柱下为工”。是说老子为周柱下史,隐于朝,终身无患,是为工(做得好)也。但是,在《非有先生论》中又借非有先生之口称夷、齐为仁者。他说:“伯夷、叔齐避周,饿于首阳之下,后世称其仁。”再是对汉武帝及其政治,心中不满,却当面吹捧。他发狂言,说自己是避世于朝廷间的隐者,其实隐含了对汉帝的不以为然的看法。如果当时是一种牢骚,是发泄对不得重用的不满情绪,那么到了晚年,而借非有先生对吴王的谈话,大谈避世原因,就含有人主不明,用人不当的批评了。
吴王问非有先生:先生来到吴地,我对你期望极高,但三年了,先生“进无以辅治,退不扬主誉”。“盖怀能而不见,是不忠也;见而不行,主不明也。意者寡人殆不明乎?”非有先生伏而唯唯,不敢说话。吴王曰:“可以谈矣,寡人将竦意而览焉。”先生说:“于戏!可乎哉?可乎哉?谈何容易!”就是说话不好说。“非明王圣主,孰能听之?”吴王一再催促。非有先生这才开口,说以关龙逢谏桀,比干谏纣,极虑尽忠,反忤邪主之心,遭杀身之祸,使贤能之士不敢进,而避居深山间。“如是,邪主之行固足畏也,故曰谈何容易!”
这明显是以古讽今,发泄对当世人主的不满,暗示出自言避世于朝的原因。
反过来又借非有先生之口,阐述自己的正面观点。拿伊尹事商汤,姜太公事周文王为例,说二人“诚得其君也”,故能成其大业。一番话说得吴王穆然,俯而深思,仰而泣下,幡然悔悟,叹说:
“嗟乎!余国之不亡也,绵绵连连,殆哉,世之不绝也!”于是勃然兴起:正明堂之朝,齐君臣之位,举贤才,布德惠,施仁义,赏有功;躬节俭,减后宫之费,损车马之用;放郑声,远佞人,省庖厨,去侈靡;卑宫馆,坏苑囿,填池堑,以予贫民无产业者。开内藏,振贫穷,存耆老,恤孤独;薄赋敛,省刑辟。行此三年,海内晏然,天下大洽,阴阳和调,万物咸得其宜;国无灾害之变,民无饥寒之色,家给人足,畜积有余,囹圄空虚……远方异俗之人向风慕义,各奉其职而来朝贺。
评说:“故治乱之道,存亡之端,若此易见,而君人者莫肯为也,臣愚窃以为过”。又引《诗》云:“王国克生,惟周之桢,济济多士,文王以宁。”此之谓也。
这段话便是东方朔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,完全是儒家王道德政的主张。但是,由于东方朔言谈放荡,以滑稽诙谐得宠,反而掩盖了他的政治才能,终不见用。后来略有所悟,但为时已晚,再发牢骚,婉转陈说也没有用了。一代饱学之士,“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”,成败皆因于滑稽诙谐。故司马迁和班固都视朔为滑稽家。
不知为什么刘向视东方朔为神仙家,写入《列仙传》,且与《汉书•本传》大不相同。一是说他久在吴中为书师数十年,昭帝时还在活动,“时人或谓圣人,或谓凡人。作深浅显默之行;或忠言,或亏语,莫知其旨。”二是说他活到了宣帝(前73~前50年在位)时,“弃郎以避乱世,置帻官舍,风飘之而去。后见于会稽,卖药五湖,智者疑其岁星精也”云云。文后有赞语曰:
东方奇达,混同时俗。一龙一蛇,岂豫荣辱。高韵冲霄,不羁不束。沈迹五湖,腾影旸谷。
刘向显然是根据后人传闻而作,并非史实,但也与东方朔的思想行为有关。
相关文章:
- [名人故事]三国时期占卜大师管辂的传说
- [名人故事]关于风水鼻祖郭璞的风水故事
- [名人故事]王阳明的五个传奇故事,跟心学宗师学做人与做事
- [名人故事]孔子的经典故事
- [名人故事]春秋经典故事之孔子占卦
- [名人故事]孔子为弟子商瞿占卜子孙后代的故事
- [名人故事]虚云老和尚最后的遗言:时光长短,唯心所造。一切苦乐,随境所迁
- [名人故事]春秋经典故事之孔子占卦
- [名人故事]一代奇人——东方朔
- [名人故事]文王“研卦”的故事
相关推荐:
- [名人故事]春秋经典故事之孔子占卦